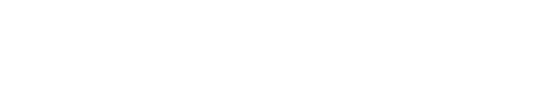專業(yè)人物
他在北大學(xué)完數(shù)學(xué),去了哪?
發(fā)布時間:2024-03-06在北京大學(xué)城市與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研究員王少鵬的生態(tài)學(xué)課堂上,他習(xí)慣于把課講得很“直觀”,而不去管一些枝節(jié)的語氣、節(jié)奏、修辭,加上他本人的鈍感,倒成了學(xué)生們口中津津樂道的“冷幽默”。
或許也正是這種“直觀”思維,促成了他從數(shù)學(xué)轉(zhuǎn)向生態(tài)學(xué)的研究。2003年,他高考考入北京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。大三,初讀利奧波德的《像山那樣思考》,從此半顆心失落在自然。碩士期間正式轉(zhuǎn)向,從事統(tǒng)計學(xué)、生態(tài)學(xué)交叉研究。2009年起,在北大攻讀生態(tài)學(xué)博士,期間前往普林斯頓大學(xué)訪學(xué)。2013-2017年期間在法國國家科學(xué)院(CNRS)、德國整合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(iDiv)從事博士后研究。2017年至今,回歸北京大學(xué)城市與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從事生態(tài)學(xué)研究,投入山野,像山一樣思考。

傾心于山之前
2003年,王少鵬進入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。當(dāng)時的數(shù)學(xué)系,常常可以看見一群青年學(xué)子為高度抽象的數(shù)學(xué)問題激情地討論。同樣是投身數(shù)學(xué),王少鵬除了思考數(shù)理抽象問題,還同時思考很多其他問題,比如著名的“保安三問”:你是誰?從哪里來?要到哪里去?
這些困惑帶有哲學(xué)意味。“上大學(xué)的時候,突然一下子面臨很多問題,都是自己原來沒有思考過的問題。”對數(shù)學(xué)學(xué)科和數(shù)理邏輯的困惑便是其中一大內(nèi)容,“中學(xué)課本上的思想,在之前看來像真理一樣,結(jié)果發(fā)現(xiàn)只是眾多的理論之一。”
幸而辦法總比問題多。王少鵬的想法很簡單:這些問題,從前一定有人思考過。于是,他泡在數(shù)院的圖書館里盡情閱覽,從書里找出口。“數(shù)學(xué)里有一個概念叫‘隨機過程’,我那一段時間思想泛濫,就有點類似這樣。”除了讀專業(yè)書,他還翻看笛卡爾的《第一哲學(xué)沉思》等書籍。某次,他隨手拿起一本小書,讀到類似這樣的一句話:“數(shù)學(xué)的統(tǒng)一性有賴于一個完備的邏輯體系,而大自然的存在本身則是所有自然科學(xué)的基礎(chǔ)。”
靈光頓閃,對數(shù)理邏輯那些極大的困惑一下解開大半。
也正是在此時,著名生態(tài)學(xué)家利奧波德的一篇散文《像山那樣思考》進入了他的世界。好像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總是會攫住他,或早或晚地。
正像當(dāng)初鹿群在對狼的極度恐懼中生活著那樣,那一座山將要在對它的鹿的極度恐懼中生活。而且,大概就比較充分的理由來說,當(dāng)一只被狼拖去的公鹿在兩年或三年就可得到替補時,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憊了的草原,可能在幾十年里都得不到復(fù)原。
初次讀到,大三的王少鵬想了很多,頭腦中一些原本整齊的思緒被攪亂了。他驚覺自己以前從未“像山那樣思考”過。利奧波德在文中闡述的原理其實并不難理解,就是今天眾所周知的營養(yǎng)級聯(lián)學(xué)說。真正讓他驚奇的是,營養(yǎng)級聯(lián)學(xué)說遠在利奧波德寫下這篇散文后十年方才建立。基于經(jīng)驗、生成于實際自然環(huán)境中的問題感,竟可以如此超前地預(yù)言現(xiàn)實中的問題!
這一下激起了王少鵬對生態(tài)學(xué)的興趣,于是他暫時放下了對于數(shù)學(xué)抽象問題的思考。
如今再提到那時的思考與選擇,王少鵬坦言:
好多問題可能在做、在讀的過程中慢慢地才會清楚;也許到最后,人一生最終結(jié)束的時候也想不清楚,但是慢慢地自己會有越來越多的答案,不是一個最終的、完整的答案,而是會對這個問題會有更多的說法。
向著山出發(fā)
大四,王少鵬開始出野外考察。研究生一年級時,他隨考察隊從北京下到云南,駐扎在哀牢山森林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國家野外科學(xué)觀測研究站,白天在研究站附近進行簡單考察。但一趟下來,每個人還是“收獲”了腳底板上大大小小十幾只螞蟥,很多甚至還活著,其體內(nèi)特有的抗凝血成分使傷口血流不止。還有一次,考察隊前面有人踢到蜂窩,王少鵬全身上下被蜇了個遍,腫包腫起來很高,而且出現(xiàn)了過敏反應(yīng)。一旁的向?qū)ё屗s緊灌風(fēng)油精——那也成為他至今難忘的味道。
盡管如此,王少鵬依舊陶醉其中,那讓他回歸童年和故里,那些親近自然、無憂無慮的時光。

2007年,王少鵬在哀牢山測量樹木胸徑
經(jīng)驗的積累,興趣的催化,逐漸堅定了王少鵬轉(zhuǎn)系的決心。那時,北京大學(xué)生態(tài)學(xué)系建系還不到十年,尚在起步之初。但北大的生態(tài)學(xué)研究,其實早在上世紀(jì)五十年代就已萌芽。從一間二十平方米、能坐十幾個人的小教室,到如今開展高水平科研、教學(xué)和社會服務(wù)工作的北京大學(xué)生態(tài)研究中心,幾十年間,幾代人的努力,生態(tài)學(xué)在北大得到蓬勃發(fā)展。但王少鵬決定轉(zhuǎn)系時,并不曾想到這些。那時的他所看到的、所想到的,只是“生態(tài)學(xué)看起來是一個很適合自己的方向”。

2007年,王少鵬前往哀牢山參加野外工作
王少鵬在數(shù)院的導(dǎo)師耿直教授素來十分支持學(xué)生自由探索興趣,王少鵬接觸并深入生態(tài)學(xué)研究,也還多虧了他——他和生態(tài)學(xué)系的方精云教授曾一同留學(xué)日本,一直希望合作帶一個學(xué)生。碩士二年級時,王少鵬正式向他提出轉(zhuǎn)系。對此,耿教授不僅非常支持,甚至很高興,因為王少鵬“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興趣”。
轉(zhuǎn)到生態(tài)學(xué)系后,王少鵬跟隨方精云教授做研究,他同樣對王少鵬產(chǎn)生了深刻的影響。“方老師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個方面,一個是方老師會關(guān)注比較大的一些科學(xué)問題,視野看得很高遠;另一個是,在確定了研究方向之后,方老師會堅持不懈地去研究,基本上他所選的方向或者題目,最后不僅能得到新的成果,還往往會有比較系統(tǒng)性的延伸。”方教授高遠的視野、堅持不懈的韌勁,至今仍為王少鵬所推崇、追尋。
在兩位老師的影響與支持下,王少鵬開始從事生態(tài)學(xué)與數(shù)學(xué)交叉研究。但是,生態(tài)學(xué)面向的問題和數(shù)學(xué)很不一樣,數(shù)學(xué)以邏輯學(xué)為基礎(chǔ),生態(tài)學(xué)更多基于歸納,從抽象思維到實體研究,在這個過程中尋找平衡點并不簡單。“我自己做可能是把這兩個東西結(jié)合起來,就是基于對野外的一些情況建立起來的經(jīng)驗認(rèn)識,再用數(shù)學(xué)的方法去做一些推演。”
探索十余年,王少鵬逐漸地找到了二者之間的平衡,一步步往前走。
此方山,異鄉(xiāng)野
博士期間,方精云教授推薦王少鵬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(xué)進行訪學(xué),這使王少鵬有機會接觸“這個領(lǐng)域最前沿的研究組”。
提到普林斯頓訪學(xué)那段時光,王少鵬又露出了他招牌式的笑容。第一次作組會報告時,“自己英語都不太行”。上臺后,他卻發(fā)現(xiàn)臺下坐著好幾位名字出現(xiàn)在教科書里的著名學(xué)者。那種對學(xué)生的重視與培養(yǎng),王少鵬至今記憶猶新。
博士畢業(yè)后,王少鵬又前往法國國家科學(xué)院生物多樣性理論與模型中心做博士后研究。研究中心坐落于叢山之間,周圍零星有幾個小村子,偏僻而寧靜。在那里,他常常站在辦公室的落地窗前,看著中心飼養(yǎng)的動物,或者爬上附近的小土坡俯瞰工作的地方。

法國國家科學(xué)院生物多樣性理論與模型中心工作站俯瞰圖
工作環(huán)境清靜,周圍環(huán)境里講英語的人不多,“只要找到一個問題、一個方向的話,也就沒有別的什么事可做了,非常專注。”也正是在那兒的兩年半里,王少鵬在研究上“有挺大的進步”,他目前研究的一些方向,也都正是在那時起步:“那邊的合作導(dǎo)師很擅長整合不同的學(xué)科分支,通過理論分析研究,在不同分支之間構(gòu)建聯(lián)系”,如今,王少鵬團隊正致力于發(fā)展這種整合性理論。
而后,王少鵬又進入德國國家整合生物多樣性中心進行博士后研究,接觸到對他而言相當(dāng)于一個新的方向的食物網(wǎng)研究,他又開始重新沉下心來了解并研究,現(xiàn)在也成為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。
由于生態(tài)學(xué)的地域性,許多研究采樣乃至實驗都必須基于特定國家的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。但研究方法與視野的共通使得科學(xué)問題跨越了國界。當(dāng)目光聚焦于土石草木,此方山,異鄉(xiāng)野,一樣美麗而迷人。
山的孩子
以青年教師的身份回到北大之后,王少鵬教學(xué)生的思路也是“立足生態(tài)學(xué)本身的問題,不要鉆到數(shù)學(xué)的求解過程去”。他總是和學(xué)生強調(diào),做理論生態(tài)學(xué)研究,先有問題、后有模型。
我們的論文都發(fā)表在生態(tài)學(xué)領(lǐng)域的期刊,沒有在數(shù)學(xué)或者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領(lǐng)域的期刊發(fā)文章,我的學(xué)生們也是。

帶學(xué)生這件事,他是認(rèn)真的。有段時間,王少鵬告訴自己,“今年不發(fā)自己為第一作者的文章”,專力為課題組學(xué)生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。學(xué)生的文章交上來都是大改,有時幾乎重寫。不過,一切很值,當(dāng)年的課題組的各位成員已經(jīng)都有了自己深耕的研究方向。
此外,他也常常推薦同學(xué)們?nèi)タ匆恍┥鷳B(tài)學(xué)方面的經(jīng)典著作。與文獻“對話”,這是王少鵬從學(xué)生時期就重視的做法,在自由的大學(xué)氛圍中,這一點顯得愈發(fā)難能可貴。不過在他看來,能夠主動探索、產(chǎn)生想法,并在主動思考中批判自己的想法,這才是做學(xué)術(shù)最重要的方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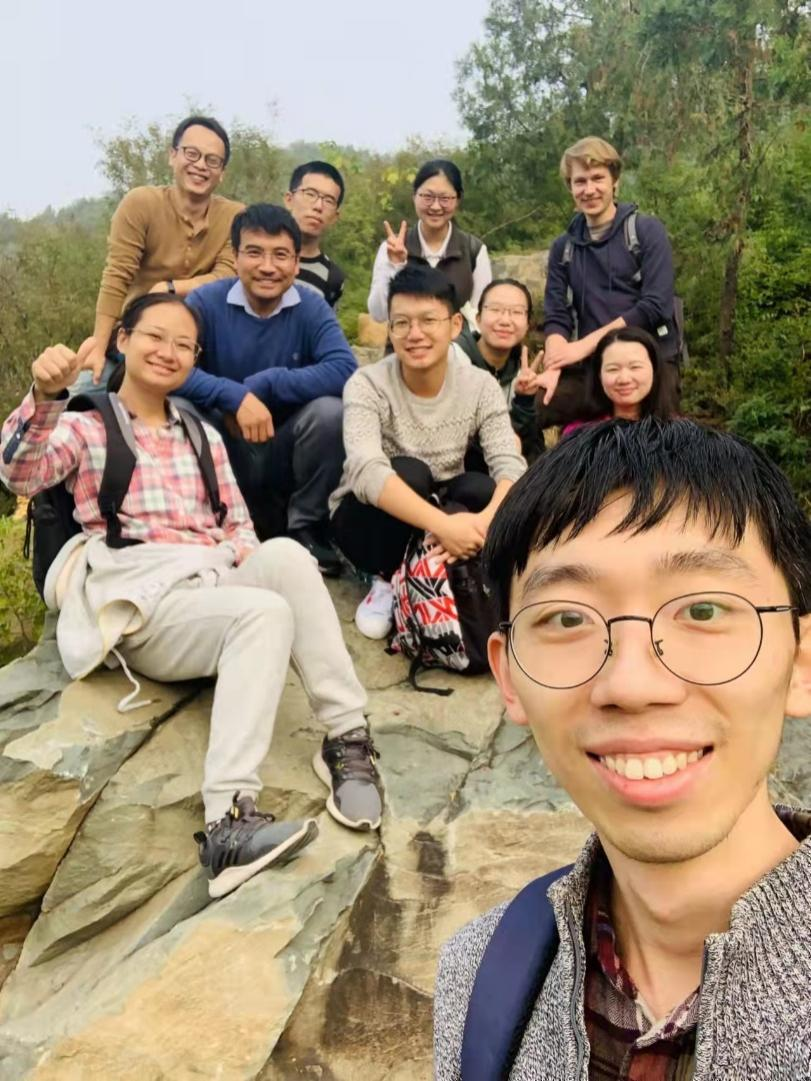
王少鵬與學(xué)生們
2013年,王少鵬在博士畢業(yè)論文后記回憶起十年前最初入北大時的場景:“2003年秋,我拿著錄取通知書第一次走進燕園。燕園的一切對于我都是新奇的,貼滿海報的三角地,西門裸地上煙熏火燎的雞翅戰(zhàn)隊,飄滿符號的數(shù)學(xué)分析課堂……那時我不曾想到,我會在這個園子里度過九年的時光。而今九年過去了,當(dāng)初一起進到園子里的那些人,都已帶著他們的故事逐漸走了出去。燕園也在進行著它自己的更新,從熟悉到陌生,又從陌生到熟悉。于我,九年卻好像很薄,只像是翻過了一頁紙。”
時間來到2023年,又一個十年流過,這十年的厚度又幾何呢?吐納更新的燕園里,是作為青年教師的王少鵬。對他而言,不變的是仍在北大做生態(tài)學(xué)研究,變化的是身后多了一群學(xué)生。
他要向他們傳遞“解決現(xiàn)實問題”的學(xué)術(shù)精神。他的課題組主頁上有這樣一段話:
我們嘗試發(fā)展新的理論并開展理論驅(qū)動的經(jīng)驗分析,以解決現(xiàn)實世界的問題,特別是預(yù)測全球環(huán)境和生物多樣性變化的生態(tài)后果。解決這些問題的挑戰(zhàn)在于發(fā)展一種整合的生態(tài)學(xué)理論框架,將密切相關(guān)但又分別發(fā)展的子學(xué)科(如群落生態(tài)學(xué)、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生態(tài)學(xué)和景觀生態(tài)學(xué))整合起來。我們的研究希望為這樣一個整合理論作出貢獻。
自初次進入山的懷抱,這一路王少鵬一邊思考、一邊實踐。如今,帶著一群又一群山的孩子,向山,像山那樣思考。
個人簡介
王少鵬,北京大學(xué)城市與環(huán)境學(xué)院生態(tài)研究中心研究員,博士生導(dǎo)師。2007年于北京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獲學(xué)士學(xué)位,2013年獲北京大學(xué)生態(tài)學(xué)博士學(xué)位。2013-2017年期間在法國國家科學(xué)院(CNRS)、德國整合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(iDiv)從事博士后研究。2017年至今任職于北京大學(xué)。研究興趣為利用理論生態(tài)學(xué)方法研究生物多樣性與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穩(wěn)定性。近期工作嘗試將BEF理論推廣至區(qū)域尺度和多營養(yǎng)級群落,并利用全球時空數(shù)據(jù)做驗證。相關(guān)成果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(fā)表在Science, 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, Nature Communications, PNAS, Ecology Letters, Ecology等期刊。現(xiàn)任Ecology Letters、Ecological Monographs等期刊編委。